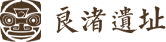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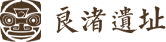

能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1981年我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我们班共有18个人,包括15个男生和3个女生。当时张忠培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林?先生做了我们的班主任。后来才慢慢知道,他们原来是那么有名的教授。其他老师私下里都称张先生为张大帅,或者大帅,意思是可与张作霖媲美的东北王。张先生开创了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现在成为考古系。听张先生说当时东北考古是空白,想要开辟那里的考古事业,所以才到了吉林大学。张先生给我们班上两门课,一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一门是田野考古学。旧石器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先生为我们讲授。这些老师们不仅传授了我们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成为我们日后做人做事的楷模。
张先生按照地区和流域将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划分成为许多的区系类型,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从早到晚梳理讲解。他不用写好的讲稿,只是列出几条提纲,讲到哪个文化就将基本的陶器组合以及变化规律在黑板上画出来,我们就跟着画图做笔记。张先生是个很感性的人,讲起课来即兴发挥,充满激情。听张先生的课是快乐而深刻的,但做起笔记来却很辛苦。一是张先生的浓浓的湖南口音,我们费了好长时间才基本上听懂先生说的是“黑陶”还是“褐陶”;二来先生在讲课的过程中,往往会举一些他读研究生时进行民族调查时的故事,或者常常讲着讲着会说“你们懂哲学吗?”然后给我们讲一通哲学。我们大家听得兴奋,个个聚精会神,可后来听先生话锋一转才知道,啊!原来这些也是需要记的课堂内容。那时大家也没有录音机,等回过神来,许多精彩的内容已经来不及记了,现在想起来真是挺可惜的;张先生上起课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常常觉得课时不够用,不过瘾,所以经常上午上完课,告诉我们“晚上接着上课呵”,晚上不受课时限制,往往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
当时还是全国统一分配,我们毕业那年,正好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个名额,但我们班没有南方同学,最后决定从陕西的四个同学里面出一个,从此我的命运就与江南连在了一起。我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分到最南边的学生。从来没有去过南方的我,怀着好奇与期待的心情,想象着江南的样子。也暗下决心不能给学校和先生丢人,于是毕业前我专门去请教张先生,问先生我到了浙江工作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今天还清楚的记得张先生说,长江下游是个独立的区域,文化面貌单纯,做考古是块好地方,可以很快地熟悉入门,并鼓励我要好好干。还说浙江的牟永抗先生等都是有学识的考古学家,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1985年的8月,我第一次踏上江南的土地,来到向往已久的西子湖畔杭州。当时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距离断桥不远的环城西路上,地理位置很好,但办公条件不太好,一座两层的简易旧式楼房,就是考古所的办公楼,省文物局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另一座小楼里。史前考古室加上我总共只有5个人,挤在二楼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室主任是牟永抗先生,另外有王明达、杨楠、芮国耀和我。虽然条件艰苦点,但对于新来的我来说,增加了不少与大家接触学习的机会。牟永抗先生与王明达先生是长辈,杨楠、芮国耀与我年龄相仿,5个人老中青三代,可谓是其乐融融。
在距离杭州西北约30公里的余杭瓶窑镇边上,有个属于我们研究室的工作站――吴家埠工作站,这里存放着自建所以来浙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物标本。工作不久,王明达先生就带着我参观了工作站,为我详细讲解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商周时期陶器的特点,使我得以在最短的时期内熟悉本地的文化面貌,至今想起来仍是十分感谢。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计划下半年要在杭州召开一个纪念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年初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开始筹划,从谋划到实施,自然落到了我们史前室的几个人身上。除了准备论文之外,为了能给纪念大会献上一份厚礼,我们一方面积极筹备发掘可能是良渚墓地的反山,希望能有好的收获;另一方面则着手整理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浙北地区发现的80余座良渚文化的小墓资料,以便开会的时候请代表们参观。为了工作的齐头并进,由王明达和杨楠先在工地发掘。牟永抗先生则带领我和芮国耀在吴家埠整理资料,我们约定一旦发现良渚文化墓葬,整理工作立刻停止,大家一起投入发掘。好在吴家埠与反山相距不远,大家可以时常相互切磋。
在整理资料的同时,牟永抗先生还给我另外两项任务,一是把从马家浜文化一直到春秋战国的陶器按时代排列摆放到文物架上,以供开会时大家观摩。二是与他共同撰写《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回顾与展望》的论文。牟先生给我讲了许多他的观点,以及必需要读的一些文章。这两项任务给了我快速成长的机会,使我从实物资料到文献理论,得以在短时期内全面熟悉起来,这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我也很快体会到了张先生所说的,长江下游地区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与完整性的发展序列。从学校到工作岗位,一路得到先生们的提携与教诲,如今想来常常感到幸运,并充满感恩。
反山的发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首先在表土以下发现并清理了11座汉代的墓葬。1986年的5月31日是值得纪念的,那天我们确认了第一座良渚大墓,反山12号墓。很荣幸12号墓从器物露头后的发掘清理工作由我来做,当手中的竹签插进土里,碰到玉器时那种硬硬的感觉,最是让人激动、好奇与期待,因为土翻起来,你不知到下面会显露出一件怎样的器物来,这也正是考古工作的魅力和快乐所在。反山12号墓出土了至今为止个体最大的玉琮和玉钺。当将那件13斤重的玉琮搬起来的时候,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今天想起来仿佛还留在手上。反山的发掘一直进行到了10月份,共发掘出土了11座良渚文化的大墓,出土陶、石、玉、象牙、涂朱嵌玉器等1200件(组)。反山的发掘是浙江的考古工作者们第一次发掘到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墓葬,而我有幸成为发掘者之一,也因此与良渚文化研究和良渚玉器研究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反山的11座大墓在排列位置上,墓坑规格上,随葬品的多寡与种类上,都反映出许多的差异和严格的规定,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与认识。将良渚文化大墓与玉器的研究,从单一的墓葬而扩展到了对整个墓地的认识,为我们从一个整体上考察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化、分工等提供了新的材料。通过反山的发掘,对良渚玉器的种类、组合与功能等的研究,有了许多新的认识,从而开辟了良渚玉器研究的一个新阶段。对以往作为兽面(或饕餮)认识的玉器上的图案,由于反山出土了它的完整的神兽结合的图像的祖形,从而在解释这一图像的内涵上,有了完全不同的角度。尽管仍有许多不同的具体看法,但将其认作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已成为共识。这一认识上的改变,对于正确解读良渚玉器的功能与造型上的意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反山的发掘还复原了玉钺的安柄形式,将以往称作“舰形器”和“杖首”的玉件,恢复到了钺柄的两端,并提出了玉钺具有权杖功能的认识。对三叉形器、冠状器等主要玉器,都找到了复合其功能的基本合理的解释依据。对良渚玉器从单一的认识,扩展到了对其组合件的认识。并且对琮、璧、钺、三叉形器、冠状器、玉璜、锥形器等玉器,从组合上和礼器系统的角度开始进行探讨。良渚玉器的研究,自此开始走向成熟。 1986年冬,在杭州成功举办了“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们参观了刚刚发掘完的反山遗址,观摩了反山出土的大量的良渚玉器。学者们对五千年的人类创造,以及玉器和大墓所反映的良渚社会的文明程度深感震撼。反山的重大发现与良渚50周年会议的召开,使良渚文化和良渚玉器的研究,从此更加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浙江的考古工作,尤其是良渚遗址的考古和保护,也日益受到国家文物局和苏秉琦、张忠培、严文明等先生的重视。从此张忠培先生和严文明先生等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先生们,每年总有几次亲临浙江和良渚指导工作。浙江省文物局还特聘张忠培先生与严文明先生为特别顾问。
198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发掘了余杭安溪瑶山遗址,在瑶山的山顶上揭露出了一座平面上呈内外三重土色结构,边缘砌有石头护坡的覆斗形的祭坛遗迹。并在祭坛上清理了11座与反山相类似的良渚文化大墓。瑶山的发掘,不仅又一次获得了大量的精美玉器,而且也为良渚文化增加了一项新的重要内容――祭坛。从而使研究者们开始注意到良渚大墓与祭祀址,良渚玉器与祭祀的密切关系。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先后发掘了庙前、梅园里、卢村、姚家墩、葛家村、塘山等一系列遗址。
1987及1992~1993年通过对莫角山遗址的发掘,认识到这个面积约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的大型土台,是良渚文化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如此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以及与反山、瑶山等大量精美玉器的联系,反映了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 。记得1992年莫角山遗址发掘时,张忠培先生与时任国家文物局文保司的孟宪民司长一同前来视察,张忠培先生考察完之后,第二天很慎重地把省文物局的领导以及我和王明达先生等约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向我们讲了他考察后的思考,以及关于良渚遗址以后保护的思路,对于良渚遗址的考古和保护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宪民司长多次来良渚之后,也对良渚倾注了特别的情感。1998年在孟司长的关心支持下,由浙江省考古所古建院做了良渚6个遗址点的保护展示方案,并在汇观山遗址进行了试点实施。
1995年张忠培先生在《文物》上发表了题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的社会阶段――五千年前中国进入文明的一个例证》的论文,提出了“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根据良渚墓葬的现象分析指出“良渚社会,已从史前的氏族组织,蜕变成了政权,进入到了国家的时期”。通过对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比较,指出良渚文化的起始年代为“距今五千二三百年,延续到公元前第三千纪前半,或约距今4600年前”。张先生这些超前的认识,对于良渚文化乃至长江下游史前文